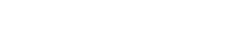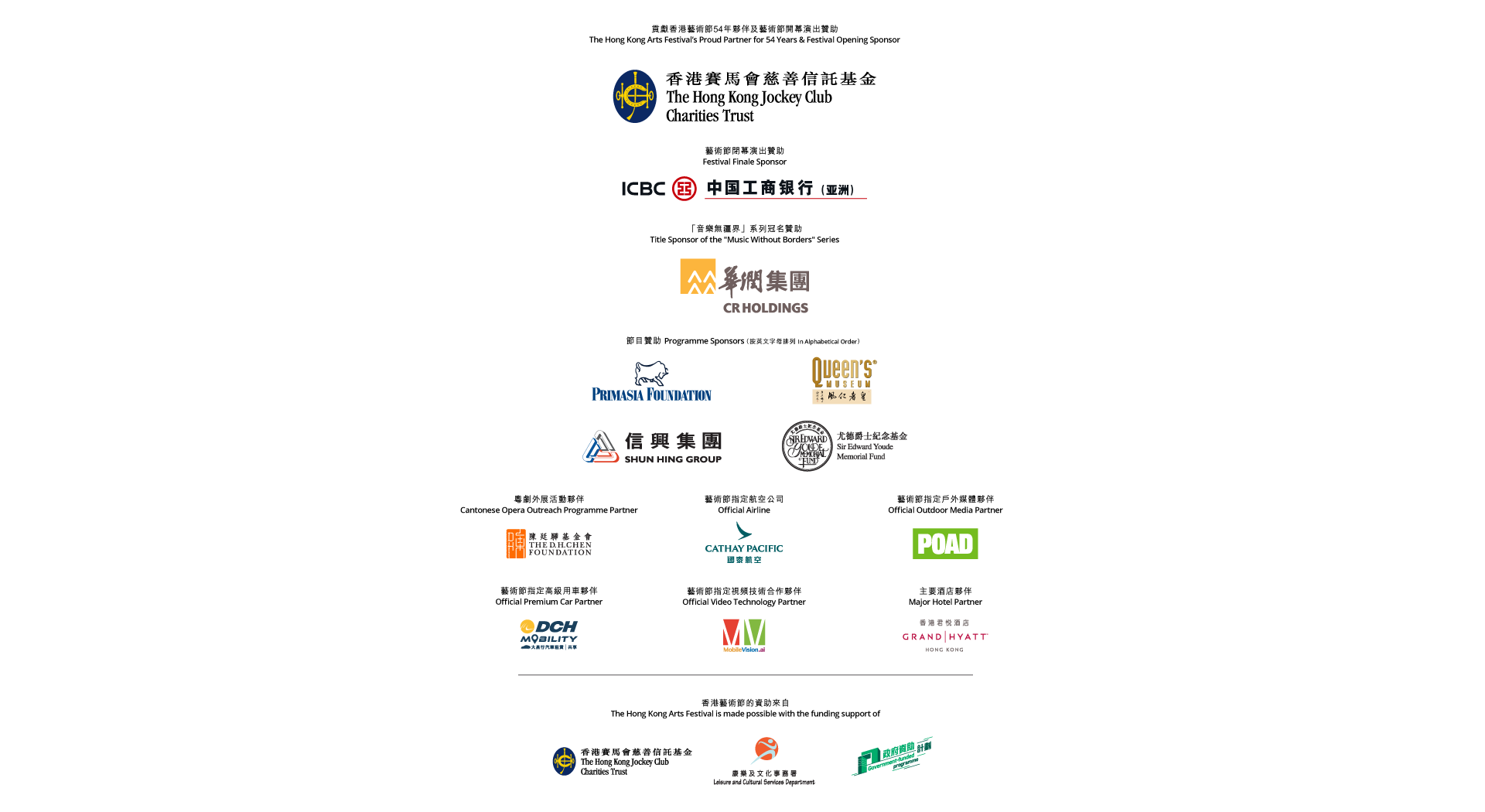在當代劇場形式中不斷尋找突破的,還有塞巴斯汀.凱撒。這位幽默的德國導演半開玩笑地提出「超貧窮極流動劇場」,以破格形式改編劉以鬯的小說《酒徒》,帶領觀眾在意識流中捉迷藏,體會藝術家在現實與理想間的永恆掙扎。

「超貧窮極流動劇場」這名堂,令人聯想起二十世紀兩位戲劇實驗大師埃爾溫.皮斯卡托(1893-1966)和葛羅托斯基(1933-1999)的理論,不過這全屬好玩的戲謔。波蘭戲劇傳奇葛羅托斯基在1970年代提出的「貧窮劇場」,他提倡剔除化妝、非自主的服飾、舞台佈景、燈光等「非必要」的元素,追求觀眾與演員直接的現場交流,告別「舞台—觀眾席」這模式,每個作品都為表演者與觀眾設計一個全新空間。
但是,凱撒說他並未直接受葛羅托斯基影響,更無意借巨匠之名借題發揮,明言一切只是自己的實驗起點和遊戲規則,「『極流動』與劇場空間有關,我們非常注重演員的表演……但這只是一個文字遊戲,可以是超貧窮、極流動、爆尷尬、勁搞笑……」他笑說。
「極流動」的想法可以再往前追溯:凱撒回想,十七世紀法國劇作家莫里哀的劇團有一輛名為「特斯皮斯」的馬車,裏頭裝着所有道具和服裝,由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落,並在戶外搭建舞台,拿出道具,召集觀眾、售票、演出。「我們現在活在全球化世界,也可製作這種完全移動的劇場,把手機、影片放映機放進手提行李,到世界各地旅行、演出。」不過實際操作,凱撒則賣關子說必須在戲場中體驗。

電影養份轉化
《酒徒》是華語文學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,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,原本在上海報館工作的主角因戰亂逃難到香港,卻被迫為生活放棄文學理想,只好以酗酒麻醉自己。雖然原著採用意識流的寫法,沒有明顯故事線,但凱撒認為這樣反而賦予他自由,方便為故事設定時序,「(《酒徒》)不像百老匯劇目或荷李活電影,一切都很清晰、有原因、沒有隨機性,劉以鬯的風格則現代得多。他用文字創造了一種與某種情感相呼應的形式,這種情感甚至比文字更強烈。這種形式對我非常有吸引力,尤其當我知道他本人不是酒鬼。」
他分析,劉以鬯只是借酒醉來發展故事,「這形式像是在某處旅行,在意識中、在香港、在酒吧、在愛的浪潮中旅行,香港這個大都市,有那麼多孤獨的人,四處奔波尋找愛情,尋找幸福。」
在構思劇本的過程中,他得知王家衛的電影《花樣年華》及《2046》也受《酒徒》啟發而拍攝,「這兩部電影是全球流行文化意識的一部分……我對亞洲文化的認識很大程度來自王家衛的電影。」
他驚嘆王家衛在電影中捨棄特定的情節,而是借用角色,例如電影中標誌性的抽煙場景,正是來自《酒徒》原著描寫司馬莉如何拿着香煙靠牆站、在酒徒的房間裏抽煙,「我們在演出中必然會以某種方式與這些電影相連繫……亦會把當中愛情橋段放進劇本中。既然王家衛能受《酒徒》啟發,我也可以被王家衛啟發吧。」他強調會找到一種解讀方式,為角色建立連貫性,讓觀眾跟隨酒徒回到舊香港,追尋在酒杯裏游泳的理想。
藝術家的永恆掙扎
劉以鬯在原著小說中寫道「文學與藝術,在功利主義者的心目中,只是一層包住毒素的糖衣」,反映了當時文人或藝術家在香港這種高度商業社會中有志難伸。凱撒在德國的經驗則大相逕庭,「在德國,我們有非常強大的劇場資助文化,我們得到資金和撥款,或多或少可以用來做想做的事,創作自由受到很大保護。我在這樣的劇場背景下長大,但我知道香港商業化得多,我肯定年輕藝術家正在為此掙扎。」
凱撒的改編中也會觸碰這些思考,他舉例說古希臘劇作家亞里斯多芬透過劇本,反思藝術家、劇場製作人與社會的關係,而戲劇大師莫里哀同樣也一生為此掙扎。「藝術家對抗現實,這是一個普遍而永恆的主題,在今天的香港也不例外。不僅對作家,對劇場製作人尤其如此。」劉以鬯所寫的掙扎,也是歷代藝術家的反思。
《酒徒》
日期:2026年2月28日至3月8日
地點: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詳情:https://www.hk.artsfestival.org/tc/programme/Sebastian-Kaiser-X-HKAPA-The-Drunkard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