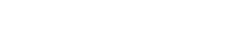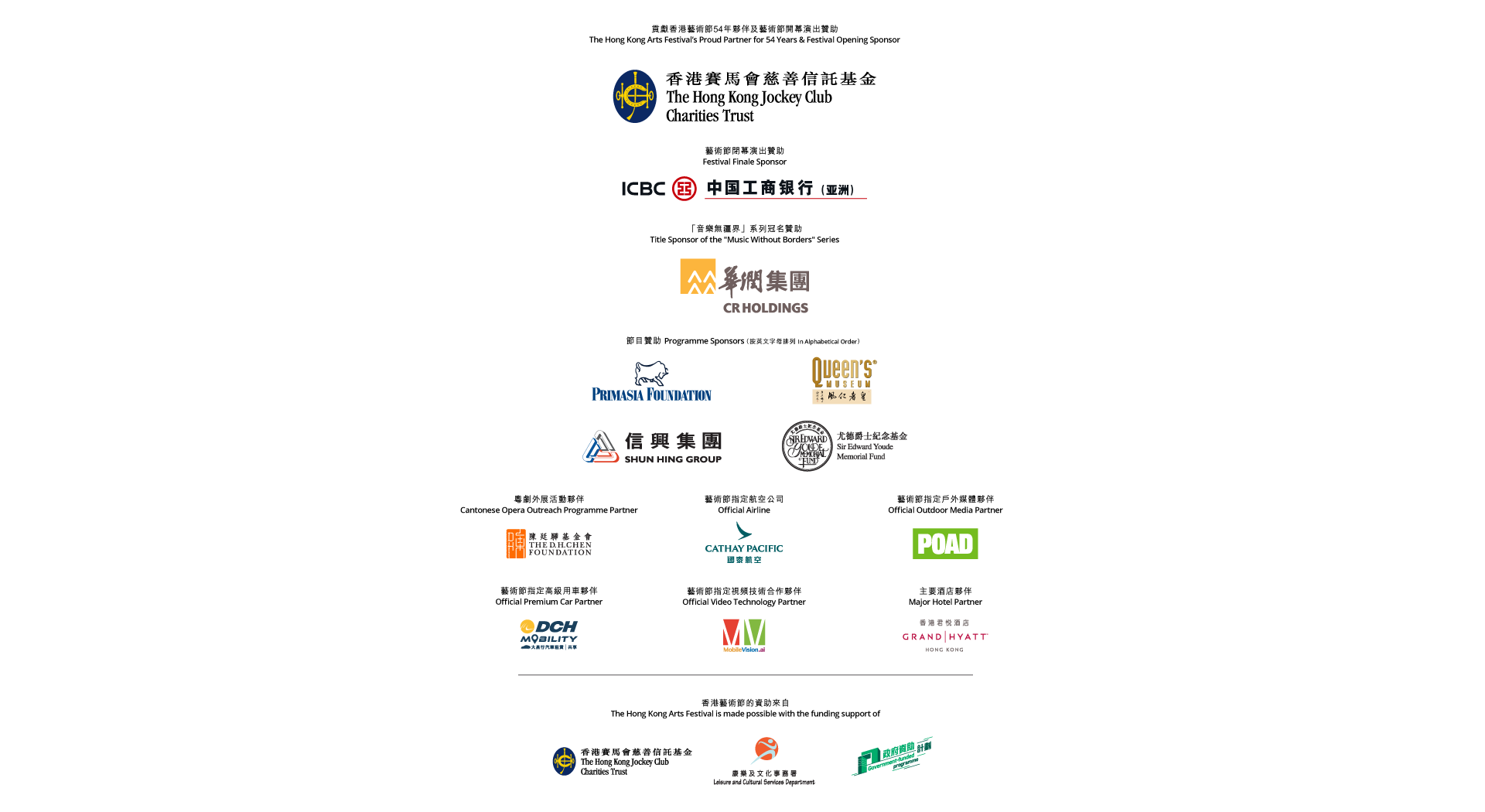在当代剧场形式中不断寻找突破的,还有塞巴斯汀.凯撒。这位幽默的德国导演半开玩笑地提出「超贫穷极流动剧场」,以破格形式改编刘以鬯的小说《酒徒》,带领观众在意识流中捉迷藏,体会艺术家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永恒挣扎。

「超贫穷极流动剧场」这名堂,令人联想起二十世纪两位戏剧实验大师埃尔温.皮斯卡托(1893-1966)和葛罗托斯基(1933-1999)的理论,不过这全属好玩的戏谑。波兰戏剧传奇葛罗托斯基在1970年代提出的「贫穷剧场」,他提倡剔除化妆、非自主的服饰、舞台布景、灯光等「非必要」的元素,追求观众与演员直接的现场交流,告别「舞台—观众席」这模式,每个作品都为表演者与观众设计一个全新空间。
但是,凯撒说他并未直接受葛罗托斯基影响,更无意借巨匠之名借题发挥,明言一切只是自己的实验起点和游戏规则,「『极流动』与剧场空间有关,我们非常注重演员的表演……但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,可以是超贫穷、极流动、爆尴尬、劲搞笑……」他笑说。
「极流动」的想法可以再往前追溯:凯撒回想,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团有一辆名为「特斯皮斯」的马车,里头装着所有道具和服装,由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,并在户外搭建舞台,拿出道具,召集观众、售票、演出。 「我们现在活在全球化世界,也可制作这种完全移动的剧场,把手机、影片放映机放进手提行李,到世界各地旅行、演出。」不过实际操作,凯撒则卖关子说必须在戏场中体验。

电影养份转化
《酒徒》是华语文学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,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,原本在上海报馆工作的主角因战乱逃难到香港,却被迫为生活放弃文学理想,只好以酗酒麻醉自己。虽然原著采用意识流的写法,没有明显故事线,但凯撒认为这样反而赋予他自由,方便为故事设定时序,「(《酒徒》)不像百老汇剧目或荷李活电影,一切都很清晰、有原因、没有随机性,刘以鬯的风格则现代得多。他用文字创造了一种与某种情感相呼应的形式,这种情感甚至比文字更强烈。这种形式对我非常有吸引力,尤其当我知道他本人不是酒鬼。」
他分析,刘以鬯只是借酒醉来发展故事,「这形式像是在某处旅行,在意识中、在香港、在酒吧、在爱的浪潮中旅行,香港这个大都市,有那么多孤独的人,四处奔波寻找爱情,寻找幸福。」
在构思剧本的过程中,他得知王家卫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及《2046》也受《酒徒》启发而拍摄,「这两部电影是全球流行文化意识的一部分……我对亚洲文化的认识很大程度来自王家卫的电影。」
他惊叹王家卫在电影中舍弃特定的情节,而是借用角色,例如电影中标志性的抽烟场景,正是来自《酒徒》原著描写司马莉如何拿着香烟靠墙站、在酒徒的房间里抽烟,「我们在演出中必然会以某种方式与这些电影相连系……亦会把当中爱情桥段放进剧本中。既然王家卫能受《酒徒》启发,我也可以被王家卫启发吧。」他强调会找到一种解读方式,为角色建立连贯性,让观众跟随酒徒回到旧香港,追寻在酒杯里游泳的理想。
艺术家的永恒挣扎
刘以鬯在原著小说中写道「文学与艺术,在功利主义者的心目中,只是一层包住毒素的糖衣」,反映了当时文人或艺术家在香港这种高度商业社会中有志难伸。凯撒在德国的经验则大相径庭,「在德国,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剧场资助文化,我们得到资金和拨款,或多或少可以用来做想做的事,创作自由受到很大保护。我在这样的剧场背景下长大,但我知道香港商业化得多,我肯定年轻艺术家正在为此挣扎。」
凯撒的改编中也会触碰这些思考,他举例说古希腊剧作家亚里斯多芬透过剧本,反思艺术家、剧场制作人与社会的关系,而戏剧大师莫里哀同样也一生为此挣扎。 「艺术家对抗现实,这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,在今天的香港也不例外。不仅对作家,对剧场制作人尤其如此。」刘以鬯所写的挣扎,也是历代艺术家的反思。
《酒徒》
日期:2026年2月28日至3月8日
地点:香港文化中心剧场
详情:https://www.hk.artsfestival.org/sc/programme/Sebastian-Kaiser-X-HKAPA-The-Drunkard